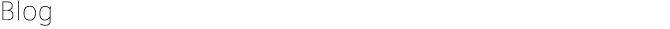【報告】《大乘起信論》與主體性:近代東亞哲學的形成與論爭
2016年1月9日,由臺灣國立政治大學(NCCU)與東京大學(UTCP)共同主催的“《大乘起信論》與主體性:近代東亞哲學的形成與論爭”國際學術會議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順利舉行。
會議首先由中島隆博教授與林鎮國教授作簡單的開場,此次研討會主題將《大乘起信論》與東亞的主體性哲學相關聯,其構想是試圖在東亞近代主體性哲學的形成過程中,找到曾經被共同關注並發揮過關鍵性影響的經典文本,藉由分疏該文本的不同詮釋與援用,以索解各種詮釋衝突背後的思想立場與走向。《起信論》在二十世紀初期,成為中國與日本佛教界的論辨焦點,並滲入了現代東亞哲學的主流論述,因此是很好的文本選擇。此之為本次會議主題的來由。
之后,迅速地進入到了會議的正題。首先發表的是來自政治大學的林遠澤教授,他以《<大乘起信論>的當代新格義——從德國觀念論轉向批判理論的試探》為題,從德國觀念論轉向批判理論的角度,提出了對以《大乘起信論》為代表的佛教的新格義。他首先指出,以德國觀念論的理論架構來理解佛教并不恰當,佛教透過緣起法或唯識的分析,來說明現象世界的「假名有、畢竟空」,這表明佛教思惟并不在現象背后預設本體或物自身的存在,這是它與觀念論的根本性差異。而批判性理論則以理性的缺陷來說明現代社會在資本主義下所產生的病態扭曲,申明了主體自由不得安頓的痛苦與解放的實踐動力,且阿佩爾與哈伯瑪斯對于康德先驗觀念論的語用學轉化表明,所謂事物的客觀實在,毋需建立在意識表象所對的物自身之上,這與《大乘起信論》中所表明的「假名有、畢竟空」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佛教的當代意義在於,若能透過批判理論的啟發,將識心的病理學診斷具體落實於對當代生活困境的批判,以大慈悲之心透過平等對待眾生,追求主體自由解放的可能性,則能具備殊勝的當代意義。
緊接著,來自東洋大學的竹村牧男教授以《井上圓了的西洋哲學與佛教理解:從東京大學<大乘起信論>講義等分析》為題,向參會的諸位介紹了明治時期成長於東京大學哲學科的學者井上圓了基於《大乘起信論》講義的學習,對西洋哲學與佛教的統合性理解。井上圓了在東京大學學習期間,從費諾羅薩、原坦山、吉谷覺壽等諸教官處接受到了西洋哲學與佛教思想的基礎教育,並在此之后認黑格爾、謝林等的哲學為最高真理,同時佛教所言說亦是與此同等的學說,尤其,他以黑格爾哲學中的“絕對與相對不二”“二元同體”之說,與《大乘起信論》中的“一心開二門”思想的類似性,將二者等同視之。井上圓了對西洋哲學與佛教的理解,也表明了明治時期日本哲學家們的別樣思想立場。
會議的第二場,由林鎮國教授所發表《<起信論>與現代東亞主體性哲學——以內學院與新儒家的爭論為中心的考察》與陳繼東教授所發表《章炳麟與 <大乘起信論>真偽之辨》組成。林鎮國教授的發言主要關注《大乘起信論》在二十世紀初期如何進入東亞主體性哲學的視域并形成影響這一問題。在他看來,《起信論》是在現代東亞各種宗教和哲學立場的競逐與爭辯中登上舞台,一是1900年前後,李提摩太(與楊文會)、鈴木大拙的英譯本之誕生,二是1902、1918年興起的,由望月信亨、村上專精及章太炎、梁啓超等人關於《起信論》成書與作者的大辯論,但更有興味的,是圍繞《起信論》所產生的思想爭辯。引發爭辯的原因在于其“唯是一心”的形上學原理,真如既超越又內在,且作為核心概念的“本覺”在《起信論》中與法身、法界等義,具備超驗性,可視為作為終極實在之主體,屬東亞佛教中上的重大理論轉折。對《起信論》的批判中,內學院的爭辯始于1922年歐陽竟無等人批評真如緣起說,認為真如只能為所緣(認識對象),正智才為能緣(認識主體),其后呂澂等人進一步提出批判。而章太炎、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基于各自的認識加以反擊,同時在語意上加以創造性轉化,意圖構建起新的主體性哲學。但在林鎮國看來,爭辯雙方其實都以“理—心”為主體的結構,在這一點上差異不大。因此,考慮到後來的語言轉向,在“理—心”之間應該安排語文的媒介,使獨我的主體成為溝通的主體,這或許或為東亞哲學帶出一條新路。
接著來自青山學院大學的陳繼東教授以章炳麟發表於《民報》的《辯《大乘起信論》之真偽》一文為線索,考察了章炳麟關於《大乘起信論》的主張。在此文中,章炳麟批評了前田慧雲、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等當時的日本學者以《起信論》非馬鳴真撰的看法,從文獻與思想的視角證明馬鳴先於龍樹。陳教授認為此種主張之背後,隱藏有章炳麟為實現中國社會變革之動機。他曾提出,一是以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二是用國粹激勵民眾(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可以推測,馬鳴及《起信論》真偽問題是直接影響其鼓吹的“革命道德”與對用文明野蠻規定國際秩序的批判的大問題。
會議的第三場首先由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廖欽彬教授開講,他以《起信論與京都學派》為題,分別討論了西田幾多郎的《善の研究》、久松真一《起信の課題》以及田邊元的晚期宗教哲學,回應或修正了袴谷憲昭、松本史朗等人所提出的「批判佛教」對京都學派的片面批判。京都學派對佛教的理解中,以西田哲學為例,松本等人認為西田的哲學中之將一切的「有」置放在一個絕對無的場所里,乃至于其後期的“場所”的無,這種不區分主客、物我、精神與物質的狀態,都被視為一種根源(ground)、基體(dhātu) ,為「批判佛教」所不喜。但在廖教授看來,這種批判忽視了,一、西田所拒絕的正是理性主體帶來的獨斷,因此提倡絕對無的“場所”;二、西田晚期的作品由“靜態的場所”轉變成了“動態的場所”,「批判佛教」并非深入到這裡。其批判的片面性在於,京都學派所談的“佛教”已經混和西方宗教與哲學而提出,而袴谷等人仍在用過去的佛教為基準進行判教。而久松真一的《起信の課題》以“即無的實存”來考察《起信論》的“真如”,唯有“真如”變成自己,才能為人覺知;而田邊元則以相依相待關係理解“空”,且他的媒介的宗教哲學,以假為空所媒介、空為假所媒介、這種相互媒介的流動正是中,意味著不會有一個真正的哲學或宗教能供人進行哲學或宗教批判的基準,因此在這一點上,足以回應袴谷等人的批判。
来自明治大學的志野好伸教授以《大乘起信論》中“起信” 的主語為何這一問題為線索,檢討了真諦譯本、實叉難陀譯本與鈴木大拙英譯本之間的解釋差異。在真諦譯本和實叉難陀譯本裡,有時用存現句以「信」和「法」等無生物表現為主語;相反,大拙譯一面徹底認為起信的主題是人,又一面始終批評人的主觀性為「妄念」。真諦譯本和實叉難陀譯本雖有不同,但皆說明了,一切眾生之內,凡夫人和初學菩薩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能主動地發起信心的是初學菩薩以上的存在,而凡夫人只有諸佛菩薩奪的助力才能經驗到自己心裡發生信心。與此相對,鈴木大不重視凡夫人與初學菩薩以上的存在之間的區別,認為一切眾生都擁有超過主觀性的主體能力。例如,借《起信論〉裡波浪的比喻,大拙稱讀此「自然」的表現,認為“全世界都澄清起來,超自然的領悟光明,像光環一樣,在我們精神人格的周圍閃耀”。也就是說,在大拙的理解中,起信被置於克服主觀性的高層次主體(“精神人格”)的支配之下。志野教授最后暫下結論,認為鈴木大拙關于主體的說明實與《起信論》的內容有大徑庭。
會議最后一場中,來自政治大學年經的博士生Jakub Zamorski發表了《唐大圓與起信論》,重點關注了1920年代居士唐大圓在印光法師的影響下,與歐陽竟無、王恩洋等人的論辯,對于歐陽、王等人對《大乘起信論》的批判,唐大圓以佛學非可固于文字之執、佛典無定法、佛理各有所宗而不應相攻詰、真如空有相成而不應執于一端、佛理不應拘于考據氣習等理由一一駁斥,此之為唐大圓對“批判佛教”之風潮下對《起信論》的維護。
最后一位發表者石井剛教授闡釋了章太炎的政治構想與《大乘起信論》的關聯性,在他看來,《大乘起信論》所闡明的,是主體既覺又不覺,非覺非不覺的中間懸掛存在方式,那是從作為本然狀態的真如被疏隔開來,但也不甘於妄然蒙昧的無明狀態的主體空間。基于這一認識,石井教授將章太炎從《大乘起信論》中獲得啟發來建構的政治哲學,作為《起信論》對20世紀初東亞哲學產生影響的一個案例,對之進行批評性分析,尤其以“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中的“隨順”一詞為核心,把握了對語言與思惟的根本矛盾與局限性的體認,論及章太炎在語言的使用上,其實無非是一個“隨順”的具體實踐過程,從《五無論》《建立宗教論》等文章中可窺見的是,其“隨順有邊”的觀念,與他同時期的“齊物哲學”一樣,對他的政治體制構想曾有過重大影響。
文責:廖娟(東京大學博士班)